谁在说话?
所谓的不言而喻,都只是自以为是。
这句话是昨天想到的。本来想用“所有的”不言而喻,但感觉太过绝对了。换成了“所谓的”,感觉温和一点。
今天课上讨论杜赞奇的时候,讲到了杜赞奇对经纪人的分类,保护型经纪人和盈利型经纪人。
杜赞奇认为,随着现代国家(这里指民国)的发展,政权内卷化出现,保护型经纪人逐渐为盈利型经纪人所取代。
算是一个小小的想法吧。
首先,一个经纪人,他可能并非二元对立的分为保护型和盈利型,这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选择题。他可能既具有保护型,又具有盈利型,他的行为具有某种场景性,他在保护和盈利之间,进行着微妙的协调。
同时,这样一个经纪人阶层,相对于“被保护人”来说,无疑具有更多发声的机会——甚至有可能垄断了发声的权力。而随着现代化的进程,这种垄断慢慢被打破。作者使用最多的史料,日本满铁公司的调查,也就是《满铁调查》,是满铁公司(大约是为了殖民做准备)做的调查。这些调查人员并非从属于经纪人阶层,他们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日后的统治,所以偏向于实用(二手观点,未读原文)。这样的后果就是,被春秋笔法隐没的“盈利性”显露了出来。
当然,建国后,这些经纪人被完全的定性为土豪恶霸,也是对“保护性”的隐没。
就像东林党人的评价,从清流到毒瘤,逐渐在发生变化。东林党事迹并没有变化,但是史家不同,史料不同,看到的事情不同。
这就引发了,在阅读史料和材料的时候,需要时刻问自己的一个问题:谁在说话?
想起了去年读布迪厄的时候,我对符号暴力做的比喻:大脑是人最重要的器官——这件事是大脑告诉你的。同理,记者和媒体是社会的良心,这是媒体告诉你的。那知识分子的神圣性,也是知识分子自己撰写的。
布迪厄对知识分子幻觉的批判,的确足够犀利,但是这种幻觉并非知识分子独有的。北京出租车司机和巷子口摆龙门的老大爷,他们的幻觉和知识分子别无二致。只是知识分子具有更多的话语权,可以把这种幻觉散布出去——而且,这种幻觉作为一种既定事实被其他人接受。
所以,知识分子幻觉值得被特别批判的原因,主要是他们得到了更多的机会说话。而且,这种话语往往被认为是客观的。或者如保护型经纪人的描述那样,被认为是“被保护人”进行的描述;但是实际上,被保护人是沉默的。
《方方日记》的争论也是如此,方方真的有为武汉人说话吗?作为一个个体,她只能为一部分人说话。最重要的是,是谁在支持她,谁又在反对她?去除掉双方(或者多方)互相扣的帽子,这些言论背后,是怎样的人?是谁在说话?
再扩大一些范围,大=任何言语都有其场景性,都有其文化背景。或者说,都认为一些东西是不言而喻的。这些不言而喻,只是作者的自以为是。(那群体的文化背景可以叫做群体性自以为是。)就像之前我对《The Age of Wild Ghosts》的评论,作者实际上预设了原始的制度更具有神圣性。这样一种反现代主义的立场,如很多人一样,属于不言而喻的价值判断。那么,正如我所说的,传统和现代之间,真的存在孰优孰劣吗?
类似这样的理论预设,是所有的作者都不会写出来的,他们认为这些是不言而喻的。而实际上,这些不言而喻的沉默来源于作者的社会文化背景,这种沉默,也是一种语言。
这种沉默,和史料一样,和作者写出来的东西一样,我想要(我们也都都需要)问一句:
谁在说话?
本作品采用 知识共享署名-相同方式共享 4.0 国际许可协议 进行许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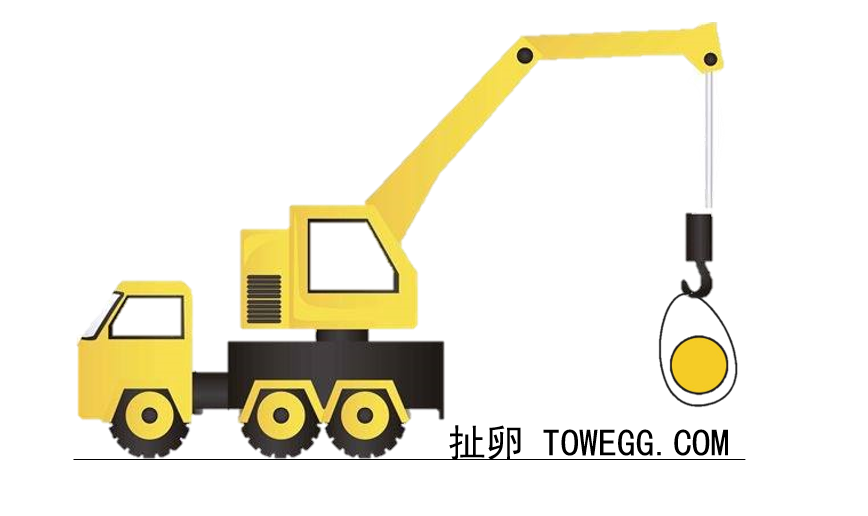 扯卵
扯卵